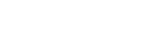《鲜花盛开的春天》 第一章 神仙眷侣 免费试读
太美的东西总让人觉得不真实,这对完美夫妻突然发生事故,她完全没有“怎么可能?”的感觉,她只觉得“终于来了”。1
都说袁振东与闻喜是一对神仙眷侣。
两人结婚十年,仍旧恩爱如初,每次相偕出现,都要引无数剩女泪满襟。
闻喜婚前曾是个知名的芭蕾舞演员,A角,领舞,直至今日团里仍有领导说起她就扼腕,说大好一个苗子,就因为结婚,二十多岁就不跳了,白瞎了一个中国的乌兰诺娃。
由此可知闻喜当年风姿。
袁振东则高大威猛,男人味十足,在知名快速消费品公司出任要职,夫妻两人感情如同找到丢失的另一边身体,身边人时时见他们听着对方的电话笑,引用袁振东助理的话说,羡慕也羡慕不来。
因为不经风雨,闻喜至今目光单纯如同少女。一般城市里三十多岁的女人,再怎么成功眼睛里都要露出点饱经沧桑来,闻喜有位离婚再嫁再离婚的女友,虽然身家丰厚,但口头禅是身上看得到的伤疤算什么?我的疤都在五脏六腑上,剖开肚子才数得到。
闻喜转述,只得袁振东一句点评:“赶快远离那个恐怖怨妇。”
当然也有掩饰得好的,不惜用各种手段留住青春,言谈举止极尽注意,又一年去两次韩国,一张脸端出来如同雪花膏,但落在别人眼里,那种用尽全力的倔强姿态最多是值得怜悯,再怎么自强不息,总带着点身残志坚的味道。
闻家妈妈最为这个大女儿自豪,所以每次到上海都拉着小女儿闻乐的手谈心,让她好好学习,努力向大姐靠拢。
闻乐今年二十八岁,佳利行商业地产高级顾问,对母亲的话嗤之以鼻。
“妈妈,那是老式妇女的想法。”
闻家妈妈“嘁”一声:“你懂什么?一个女人最幸福是经济有保障,又有老公疼,其他全都是狗屁。”
闻乐目瞪口呆:“妈,你说粗话。”
“我说粗话怎么了?我说南斯拉夫话你爸也会点头应着。”
闻乐无语,隔天找李焕然诉苦。
“这世上最可怕就是幸福的已婚女人。”
李焕然正在整理照片,他刚从甘肃回来,与一群搞摄影的朋友自驾去拍千年胡杨林,专挑平常人不走的偏僻地方去,带回照片无数,所以这几天都足不出户在整理,闻言头也不抬道:
“最可怜的是她们丈夫。”
闻乐想一想,说:“也可能他们乐在其中。”
李焕然撑着额头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闻乐一愣,然后哈哈大笑,扑过去咬李焕然的脖子。
“来,被害人。”
李焕然坐在一张转椅上,被她扑得往后退出去老远,椅子在满是杂物的地面上倾倒,两人摔到地上,闻乐仍旧压在他身上,李焕然大叫。
但她仍然不放过他,骑在他身上一定要在他的脖子上留下牙印子。李焕然举起两手投降,屋里只有电脑桌上一盏台灯亮着,闻乐乱乱发梢在他皮肤上摩擦,她刚吃过一只桃子,呼吸里还带着粘腻的甜香味,天气不正常,十月里还热得叫人冒汗,他的租屋又太乱,要命的对比出她白色丝衬衫的一丝不苟与格格不入来。
他听到自己变得短促而粗重的喘息声,那声音在窄小的租屋里产生的回响简直是致命的,他决定不再忍耐下去了,翻身把她压到了自己身下。
闻乐发出一个短暂的声音,但很快就被他吞进嘴里,李焕然在家里光着上身,穿一条宽松到危险的运动裤,闻乐觉得他是故意的,这样她就可以轻易被他若隐若现的流畅腰线诱惑到,而那些一直延展到宽松裤腰下的肌肉线条,更是令她无法自制的意乱情迷。
她把手放上去,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已经如钢似铁。
但就是在这样两人都要被**焚身的紧要关头,他们还一同开口说了句:
“安全套。”
然后同时笑了出来。
闻乐与李焕然相识于某个无聊的朋友聚会,或许也有有趣的人,但他与她已经看不到了。
他们彼此欣赏,在某方面可谓水**融,但闻乐很清楚,李焕然不是个好的结婚对象。
所有年轻摄影师都是不羁的浪子,就像他们拍的照片,再美丽也只能看看,不过闻乐不在意。
闻乐的名言是:结婚杀死原来的你。
他们一拍即合。
2
闻乐得出这个结论是有理有据的,最明显的参照物就是她的姐姐闻喜。
闻乐从小是看着姐姐为艺术献身长大的,闻喜八岁就开始学舞,别人舞鞋一两个月换一双,她两个礼拜就能穿烂,姐妹俩睡一个房间,她常看到姐姐流血的脚趾,吓得抱着妈妈说我一辈子都不要学芭蕾。
但闻喜热爱舞蹈,别人练三个小时就觉得吃足苦头,她可以在练功房里从早跳到晚,一个动作反复上百遍,不但不觉苦,还乐在其中。
闻喜生得清秀,又不爱说话,平时在人群里并不引人注目,可只要一穿上舞鞋就仿佛聚了光,那张白瓷小脸微微扬起,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美。
不要说异性,亲妹妹都爱上她。
闻乐十五岁的时候,舞蹈学院汇报演出吉赛尔,闻喜头次登台领舞。闻乐那时候正值少女叛逆期,照闻家妈妈所描述的,正是人憎鬼厌的时候,剪个寸短的头发,穿男式大衬衫,短裤短得藏到衬衫下头去,远看就像光**出门,兼之看全世界都不顺眼,姐姐第一次正式演出都要父母耳提面命勉强出席,但坐在席下看到吉赛尔悲伤死去,顿时潸然泪下。
好的艺术都是能够穿透人心的,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
闻乐满以为自己的姐姐能够成为一代大师,至少也要像一朵花那样,在舞台上盛开许多年,没想到第二年闻喜就结婚了,从此退隐。
闻乐扼腕。
她完全不掩饰自己对袁振东的不满之情,婚礼上还敲着他的肩膀说:“把我的姐姐还回来。”
被父母一顿好训。
袁振东对这个小姨子倒是好脾气,搂着闻喜一个劲儿地笑,他结婚时整三十岁,真正高大结实,立在身段纤细的闻喜身边如同一座大山,一只手总不离开她的肩膀或者腰,坐下时一定伸展手臂放在她的椅背上,又喜欢抚弄她的头发。闻喜从小脾气好,头发也软,从前盘一个圆圆发髻,认识袁振东以后就一直散着,任他长长手指绕了一圈又一圈。
李焕然曾经为某杂志拍过这对知名伉俪,回来一句点评:百炼钢化绕指柔。
闻乐嗤之以鼻:“肉麻当有趣。”
李焕然也有些好奇,半夜耳鬓厮磨的时候问她:“难道他们都是在人前做戏?”
闻乐又维护家人:“平时也这样。谁做戏一做做十年?”
李焕然顿时唏嘘:“竟然真有人可以热烈十年。”
闻乐咳嗽一声:“奇葩。”
闻乐与李焕然一样都是感情的悲观主义者,觉得爱情是流星一样不可捉摸以及易逝的东西。闻乐有过初恋,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两人是同学,大学时对方选了医科,分手前跟她说他加入无国界医生团体自愿去津巴布韦一年,她感动得眼泪汪汪,机场告别时还与他抱头痛哭,对他说你放心,我等你回来结婚。没想到三个月以后就有人在市内看到他派发喜帖,当然,喜帖上的新娘不是闻乐。
闻乐有半年除工作以外不肯出门见人。
闻喜急得团团转,袁振东都看不过去了,蹲在小姨子面前说:“姐夫替你去出气。”
闻乐仰头躺在姐姐家庭院里的躺椅上,用一本书盖住脸正似睡非睡,闻言差点跌下来,气咻咻道:“都半年了你才说这句话?”
袁振东挠挠头:“我以为漂亮女孩子都会很快恢复。”
闻乐张大嘴,对闻喜挥手:“姐,你老公对我说甜言蜜语。”
闻喜也走过来蹲下:“不如让他为你安排新一轮约会。”
闻乐最吃不消这对夫妻同心同德的样子,就连他们养的金毛狗都来凑热闹,一式一样蹲到一起看着她,她哭笑不得地挥动双手。
“走开走开,我才不要姐夫安排,他的朋友都可以做我叔叔。”
袁振东伤心,拉着闻喜的手说:“乐乐嫌我老。”
还要闻喜安慰他:“我不嫌弃你。”
闻乐仰天长叹,立刻决定恢复社交生活,当晚就遇见李焕然。
李焕然汗津津地躺在闻乐身边,眼里仍有尚未褪尽的情欲。
他把嘴唇贴在闻乐脸颊上,低声笑:“真要多谢袁先生与袁太太。”
他呼出的热气让闻乐半边脸都是麻痒的,她轻哼着笑出来:“嗯,我替你转达。”
两人不再作声,闻乐翻个身,把后背贴在李焕然的胸口上,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和他重叠在一个位置上,此起彼伏地跳着。
这个姿势让两个人都感到舒适,李焕然收拢手臂,让闻乐靠得更紧一些,然后闭上眼睛。
他听到闻乐叹气,她说:
“可是我有些担心他们俩。”
3
“担心什么?”
“他们至今没有孩子。”
李焕然想一想,因为对那对夫妻感觉实在好,难得没有冷嘲热讽,只说:“大概是不想让第三者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闻乐却喷笑出来,用力拍打他的手背。
“哪对恩爱夫妻不想要一个孩子!”
李焕然吃痛,大叫收回手:“闻乐你简直野蛮人。”
闻乐翻个身把手放在他的危险部位:“有胆再说一遍。”
李焕然正是年轻而敏感的时候,被她这样惺忪作态的一抓,立刻又有了反应,虽然还在叫,但声音已经变了样,深深吸口气,眼睛都半眯了起来。
闻乐好气又好笑:“你这个禽兽。”
他抓住她的手,让她十指再圈紧一点,低声喘息道:“正好配你这个野蛮人。”
等闻乐从李焕然那张宜家单人床上下来的时候,都是第二天中午了。
她是被自己的手机**惊醒的,迷迷糊糊从包里翻出来要接,那头已经挂断了。
她打开看,三个未接电话,都是袁振东打来的。
闻乐愣一愣,第四个电话就打过来了,然后手机屏幕一闪,接着就是一片漆黑。
她的手机没电了。
闻乐叫了一声。
李焕然惊醒,迷迷瞪瞪坐起来:“怎么了?”
“手机,你的手机呢?我要打电话。”
李焕然头发凌乱眼神茫然地看着她,跟着重复了一遍:“手机?”
这个男人没有睡醒的时候等同于无知幼儿,闲来无事的时候还觉得可爱,真要派他用处了简直能要人命。闻乐干脆地闭上嘴,自力更生地开始翻找他的手机。
李焕然独居,三十多平方米的小一居,进门就是桌椅床,但真是乱。沙发上堆满了换下未洗的衣服,空啤酒罐四处可见,垃圾从墙角的纸篓里漫出来,几个开着口仍有残渣在里面的泡面桶滚落在地上,与吃空的比萨纸盒子挤在一起,墙上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到处贴满了海报与照片。闻乐扑在沙发上将李焕然的外套裤子一顿翻,却哪里都找不到他的手机,她站起来环顾四周,突然一阵不敢相信。
这就是她在夜里觉得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幸好李焕然已经清醒了,坐起来一边套他的运动裤一边说:“我手机在摄像包里,不过也几天没充电了。”
闻乐找出来看,果然也没电了,幸好李焕然还有充电器,插上就能用了。
她打电话给姐夫,袁振东立刻接了,语气很紧张:“谁?”
闻乐赶紧解释:“是我,乐乐。我手机没电了,姐夫你找我?”
袁振东如遇救星,立刻说:“乐乐,你姐在你那儿吗?”
“不在啊。”
“她不见了。”
闻乐匪夷所思:“你确定?”
“我出差回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她手机都在桌上。”
“顺顺呢?”
“也不在。”
闻乐咳嗽一声:“她是去遛狗了吧?”
“遛到中午?”
“或许她迷路了。”
袁振东怒了:“她迷路狗也知道回家啊!”
闻乐想想也是,突然心里一动,直接问:“你跟她吵架了?”
袁振东不说话了。
闻乐没好气地:“所以她离家出走了?”
袁振东沮丧地:“你不知道事情经过。”
闻乐已经在穿衣服,一只手拎着自己的衬衫夹着电话说:“你等我,我过来找你。”
闻乐在去见袁振东之前先回了自己的住处,她得换套衣服,然后给手机充上点电。
夫妻吵架是常事,不吵才可怕,闻喜脾气是好的,但脾气好不代表她没脾气,闻乐也见过她发怒的样子,照样是只雌老虎。
以前她还担心:“姐夫那么高大,真吵起来一定是你吃亏。”
直到看到袁振东手背上脖子上被咬出来的牙印子,那是真咬,血都出来了,连肿一个星期,袁振东不得不大热天把衬衫扣到喉咙口,还对小姨子诉苦:“再狠一点就到大动脉了。”
闻乐那时候才十九岁,看得心里发怵,还要力挺自己姐姐,假装镇定地回答:“打是亲骂是爱,最爱就是咬一口,我们家的女人都这样。”闻喜在旁边笑嘻嘻,仍旧是温文尔雅的模样,一点都看不出下过那样的狠手。
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一点都不为闻喜担心,就连她都受姐姐影响,与男友情到浓时,只想着咬一口才过瘾。
佳利行是做地产的,员工住宿也有福利,她与两个同级的女同事住三室两厅的酒店式公寓,就在市中心,条件当然比李焕然的租屋好得多,但她不打算把他带回来。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她不想让别人看轻。
说到底,李焕然也不是她的正式男友,他们只是各取所需的关系,她不打算把他介绍给任何人。
闻乐下了出租车,步子匆匆地往小区里走,刚走到中心花坛就停下了,睁大了眼睛叫:
“姐!”
4
闻喜被一堆老人孩子围着,一点都看不出离家出走的凄凉,闻乐奔过去,正看到顺顺在表演它的绝技——在地上缓缓打滚。
闻乐掩面不忍。
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狗,闻喜反射弧长,养的狗也不机灵,人家金毛会叼飞盘会分左右爪子与人握手,最差也能替主人叼双拖鞋。她养的顺顺只会打滚,还滚得不甚敏捷,肚皮朝天的时间极长,简直不堪入目。
闻喜已经看到妹妹,站起来跟她打招呼。
“乐乐。”
闻乐一手牵起顺顺,不让它继续丢人现眼下去,另一手抓住姐姐,一路冲进电梯才气咻咻问:“出什么事了?姐夫欺负你?你干吗要带着顺顺离家出走?”
闻喜眨眨眼,她生得小巧,闻乐十五岁就比她高出许多,从前闻乐到舞蹈学院去找她,练功房外听到男孩子说:“看到闻喜就想背着她走。”
旁边人附和:“总觉得她弱不禁风。”
所以闻喜从小到大一路被异性关照,个个发自内心,都觉得应该多照顾她一点。引得她身边许多同性饱含酸味地评价:“男人眼里只有闻喜是女人。”
但真正的闻喜并不像外表这样柔弱,至少从前不是。闻乐与姐姐十几岁就到上海读书,一直住宿,小时候有事都是姐姐为她出头。她还记得当年她被人诬赖考场作弊,差一点被取消保送入重点高中的资格,闻喜硬是跟了校长一个星期为自己交涉,每天一早就站在校长办公室外头,不被接见又在放学时立在校门口等,每次只重复一句话:
“我妹妹绝不可能作弊,请给她重考机会证明清白。”
还有她刚进芭蕾舞团的时候,不知被多少人暗地排挤,她回来说一句:“失败不可耻,认输才可耻。”然后隔年就升了领舞。
她有一种安静的执拗,比任何大吵大闹都更有力量。
可自从嫁给袁振东之后,闻乐觉得自己姐姐越来越有心智退化的趋势,许多事想法简单得像个孩子。当然,能够十年如一日地活得像个孩子是幸福的,因为一个女人只有有人想去依靠并且那个人足够强大能够让她依靠才有资格孩子气。就像闻喜,结婚十年,现在跟人说话,脸上总像是带一点茫然之色,反应常常慢半拍,口头禅是:“那我问一下我老公。”
闻乐是习惯了在职场上东挡西杀的,与人说话听三分想七分,坐进会议室两眼一股凌厉气,转头再看自己老姐,少不得一股悲凉,也不知道是同情她还是同情自己。
闻喜回答:“我只是来找你聊聊。”
“你连手机都没带出来,姐夫打爆我的电话。”
闻喜点点头:“我想安静安静。”
闻乐噤声。
她肯定这次是大问题。
姐妹俩开门进屋,周日,闻乐的两个室友都不在,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地板擦得发亮。
闻乐关上门:“你可以跟我说了。”
闻喜看看她:“你不要换件衣服?衬衫上都是灰印子。”
闻乐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然后想到昨晚在李焕然家地板上的激烈。
她立刻就脸红了。
闻乐进卧室去换衣服,她脱了衬衫,又弯腰把手机插上电,然后迟疑了一下,想要不要给袁振东发个消息。
但她只用了一秒钟就放弃这个念头,她决定先听姐姐把事情说完,无论如何她要站在自家人这一边。
闻喜的声音从外头传进来:“这么干净,谁做的家务?”
“清洁工。”闻乐回答。
这句话又让她想到了李焕然那间凌乱无比的租屋,真该给他找一个钟点工人,但那不是她该管的事情。
李焕然在某些方面像只敏感的刺猬,他上一个女友趁他工作时拿钥匙进屋替他彻底清洁屋子,他回来大发雷霆,说她试图掌控他的生活,直接与她分手。
闻乐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个故事,当时就想,这年代谁还做田螺姑娘谁就是傻子。
她换上简单的家居服,走出来跟姐姐说话。
“好了,现在可以说了。”
5
闻喜开口,眼睛却看着窗外头。
闻乐所住的公寓在二十七层,又在小区当中,看出去密密麻麻全都是一式一样的大楼和窗户,谈不上任何风景,但闻喜就是不把目光调回来。
气氛凝重,闻乐心中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她勉强笑道:“到底怎么了?姐夫欺负你?没有接你的电话?还是说错话让你生气?”
闻喜用一种并没有太大起伏的声音说:
“振东在外头有人。”
闻乐脸上的表情完全僵住,然而眼睛却出卖她的心声。
闻喜却在此时把脸转过来,与她目光相对,数秒之后突然垂下眼笑了。
“看,连你都觉得终于来了。”
“……”
闻乐突然觉得姐姐纤细身体已经无法支撑坐姿,惊吓中起身过去坐到她身边,一把搂住她的肩膀。
她连“事情究竟是怎样”都无暇说,开口就是:“姐,无论如何我都站在你身边。”
话虽这样说,但所受的冲击却让她声音都变了调。
还要闻喜反过来安慰她,抬手按在妹妹的手背上:“乐乐,不要害怕,这样的事在世上每天都重复一亿遍。”
闻乐吸口气,要自己冷静下来,再开口直奔主题。
“你怎么发现的?”
这句话说出口,她也觉得吃惊。
袁振东是个太好的姐夫,这些年对她十分亲厚,傻子都明白这叫爱屋及乌,但闻喜说他有二心,她竟没有一点质疑。
闻喜说得不错,就连她都觉得这件事终会发生,太美的东西总让人觉得不真实,这对完美夫妻突然发生事故,她完全没有“怎么可能?”的感觉,她只觉得“终于来了”。
闻喜轻声道:“对方上门来见我,要我让位。”
闻乐只觉得一股浊气倒灌上脑门,整张脸猛地涨红,呼一声站起来猛拍桌子:“有这种事情!哪来这么嚣张的小三,简直**!”
闻喜拉住她:“你不要激动。”
闻乐匪夷所思:“不要激动?我听得都要脑充血,走,我们去找袁振东理论!”
“现在不,我需要一点时间回神。”
是真的,闻喜早晨开门见到那个年轻女孩子,骄傲又美丽的脸,从上往下又自下而上地打量她,她都不用多说一个字闻喜就明白一切,她有一种脸上被人迎面拍中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的灵魂至今不知在哪个太虚空间震荡,实在不宜处理任何事情。
但她仍旧记得早晨那短短十几分钟发生的一切,那女孩打量完她,用一种轻蔑语调说:“原来不过如此。”
闻喜与她面对面,奇迹一样,外表居然还能保持镇定。
她只记得她真正年轻。
她甚至可以在晨光中看到她脸上细密的茸毛,她几岁?十九?二十?是可以任性以及不顾一切的年纪,因为觉得青春正长,而且永无止境。
其实都是幻觉。
她还看到她插在口袋里的两手握成了拳头,肩膀绷得紧紧的,一条腿一直在不自觉地小幅度晃动。
她很紧张。
闻喜回想自己的少女时代,她问自己可曾这样不顾一切,答案是没有。
闻喜入定那样,对方反而忐忑起来,换一只脚重心站立,提口气又道:“你知道我是谁吧?布鲁斯一定对你说起过我。”
闻喜要隔一秒才想起布鲁斯是袁振东的英文名,袁振东在外资企业工作,办公室名牌都用布鲁斯袁,但他在家里从来不说洋文。他还曾说过自己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叫杰克,然后到美国进的头一个公司又自称丹尼。
中国男人的洋名字总是随意到俯仰皆同,袁振东说他在大学里认识十八个杰克,然后到美国又连相熟的唐人街中餐馆帮工都叫丹尼。
所以他见她第一面就郑重重复:“闻喜,我叫袁振东,振作的振,东方的东,请叫我振东,务必。”
她这样一叫就是十年。